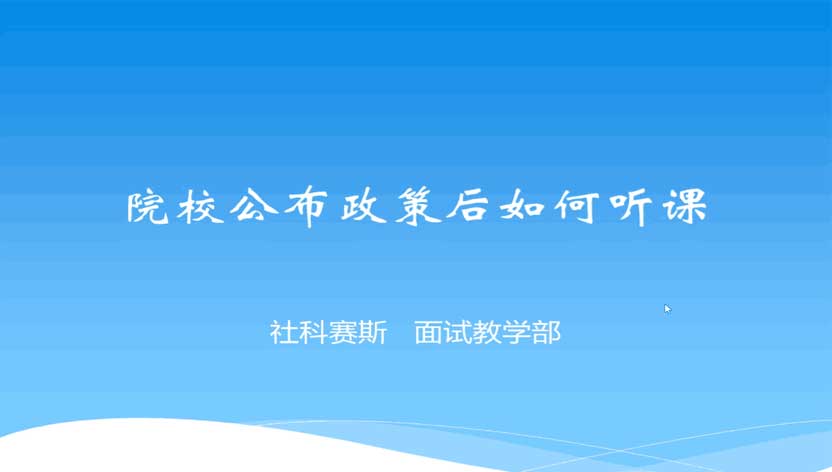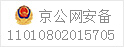2025MBA報考測評申請中......
說明:您只需填寫姓名和電話即可免費預約!也可以通過撥打熱線免費預約
我們的工作人員會在最短時間內給予您活動安排回復。
導讀:對于謝麗爾·桑德伯格來說,生活從來都是最優解。她擁有最好的資源:家世、智商、學識、財富,她站在高處,是人生的贏家。
謝麗爾·桑德伯格,Facebook的首席運營官,她曾經是克林頓政府財政部長辦公室主任、谷歌全球在線銷售和運營部門副總裁,現在是Facebook的首席運營官,也是福布斯上榜的前50名“最有力量”的商業女性精英之一。而對于中國的廣大讀者來說,她因為寫了鼓勵女性勇敢爭取事業成功的《向前一步》而聞名。
她曾在書中寫到:“伴侶的支持非常重要,絕大多數的成功女性都擁有一位相當支持自己事業的人生伴侶。”現實也確實如此,就在桑德伯格的事業步入正軌之時,她遇到了自己一生中的摯愛,在雅虎做高管的戴夫。你可以說桑德伯格是幸運的,因為她找到了這樣一位完美伴侶,支持自己的事業,又分擔了照顧家庭的責任。
然而,人生的拐點總在高潮之處,2015年5月,謝麗爾的丈夫戴夫·高德伯格突然去世,謝麗爾的世界也隨之崩塌,她認為自己和孩子們再也不會有真正純粹的快樂了。
戴夫去世兩周后,當孩子們準備參加學校的親子活動卻沒有父親的陪伴時,謝麗爾痛苦地對朋友說:“我只想要戴夫。”朋友說:“既然選擇A已經不存在,你就只能考慮選擇B了。”
這時,謝麗爾明白了,每個人都有可能面對人生中的選擇B,遇到創傷后我們需要充分了解選擇B,勇往直前,重新找到快樂與幸福。
她把自己愈療的過程寫進了《另一種選擇》當中,她希望可以幫助人們“不必經歷悲劇,就可以提前建立自己的復原力,為面對潛伏在人生前路的障礙做準備。”
今天,小編要為大家推薦的正是謝麗爾·桑德伯格的新作《另一種選擇》。希望可以對你有所啟發。
當我們用各種不同的方式面對或處理消極事件時,也播下了復原力的種子。
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花了數十年研究人們如何應對挫折,結果發現有三個認知因素會阻礙復原力:
(1)個人化(personalization):認為壞事的發生都是自己的錯;
(2)普遍性(pervasiveness):認為消極事件會影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3)持久性(permanence):認為事件的殘余效應將永遠存在。
這三個因素(簡稱“3P”)的存在,它們會讓你的大腦縈繞著這樣的想法:“都是我的錯!一切都糟透了,人生糟透了,而且會一直糟下去,直到永遠!”
認識到消極事件并非個人原因所致,困難也并非無處不在,更不會永久存續的人,患抑郁癥的可能性會降低,也會更好地渡過難關。
認為壞事的發生都是自己的錯
我也曾落入3P陷阱,首先是從個人化的內疚開始的。
戴夫去世后,我迅速陷入了自責。第一份醫學報告顯示,戴夫的致命傷是從健身器械上跌落導致的頭部損傷。因此,我不斷地責備自己,如果我們早一點兒發現,他就能夠被救活了。
我的弟弟戴維是神經外科醫生,他堅持認為我這么想是不對的——從健身器械上跌落下來,可能會讓戴夫的手臂骨折,卻不會要了他的命,所以,在他跌落之前一定發生了什么。
后來的尸檢證實了戴維是對的,戴夫死于因冠心病導致的心律失常。
即便如此,我仍能找到其他理由責備自己。
此外,我還因為他的去世給我身邊的人帶來的不便而感到自責。悲劇發生之前,我是家里的大姐、實干者、計劃者、領導者,但戴夫離開后,我突然什么都做不了了。
接下來的幾個月,我發現自己說得最多的一話是:“對不起,我很抱歉。”我不斷地跟每個人說抱歉。
我的朋友亞當最終說服我,我必須舍棄“抱歉”這樣的字眼。他也提到,其他類似的閃爍其詞的表達也不能再使用。亞當解釋說,自責會阻礙我復原,這意味著孩子們的復原也會受到影響。他的話讓我驚醒了。我意識到,既然醫生都沒能阻止戴夫的死亡,那么我相信自己有能力阻止他的離開就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我也沒有打擾任何人的生活,所有的不便都是悲劇的發生帶來的。
當自責越來越少時,我開始注意到,并不是每件事都那么糟糕——孩子們可以整夜熟睡了,他們哭得少了、玩得多了;我們也去找專業的咨詢師和治療師尋求幫助,我可以自己照顧孩子們了。我有深愛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他們每時每刻都為我和孩子們提供支持,我感覺跟他們更親近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親密。
認為消極事件會影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戴夫去世10天后,孩子們就回到了學校,我也在他們上學的時候返回了工作崗位。回到工作崗位最初的日子非常混亂。
我在Facebook(臉書)擔任首席運營官超過7年,但是,突然間,一切都不一樣了,變得很陌生。當天第一個會議上,我能夠思考的只是:“每個人都在講什么呢?這個會議有什么意義呢?”
然后在某一點上,我被拉入討論——突然有一秒,也許是半秒,我忘記了一切,忘記了死亡,忘記了戴夫躺在健身中心地板上的樣子,忘記了棺木下葬的場景。那天第三個會議上,有幾分鐘我竟然睡著了,但我對此也感到慶幸,因為是這幾分鐘是戴夫去世后,我第一次感到放松的時刻。幾周過去了,幾個月過去了,我可以更長時間地專注在工作上。工作給了我一種做回我自己的感覺,同事們對我的善意也讓我知道,我的生活并沒有那么糟。
我一直相信,人們需要在工作中得到支持和理解;我現在更加深刻地體會到,悲劇發生之后這一點更為重要。
我想起我大學畢業之后,第一天到公司上班,老板讓我在 Lotus 1-2-3(一款 90 年代很流行的電子表格軟件)里輸入數據,我表示自己不會。老板怒道:“你連這個都不會,是怎么拿到這份工作的?簡直難以置信!”緊接著,他摔門而出。
那一瞬間,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懷疑,甚至以為自己要被解雇了。但之后我明白,我只是不擅長電子表格軟件而已。
認為事件的殘余效應將永遠存在
在3P陷阱中,對于我來說最難的部分是悲傷的持久影響力。
數月以來,無論我做什么,我都會感覺到痛苦無處不在。我認識的大部分經歷過人生悲劇的人都說,隨著時間的流逝,悲傷會慢慢消逝。他們想讓我相信,總有一天,我會微笑著想起戴夫。但我根本不相信。孩子們哭的時候我會迅速想象到未來——他們未來的生活中沒有爸爸了。
當我們受苦的時候,便傾向于將苦難無限地投射、放大。
有一項叫“情感預測”(affective forecasting)的研究,旨在對人們未來的情緒進行預測。該研究顯示,我們往往過度放大了消極事件對于自身的影響。
研究人員請一些學生想象自己和愛人分手兩個月后的傷心程度,又請一些真正經歷過分手的學生報告分手兩個月后的感受。研究結果顯示,真正經歷過分手的學生要比僅憑想象的學生更快樂。此外,我們也會高估其他壓力事件的消極影響。例如,被拒絕授予終身教職的助理教授,認為自己在接下來的5年內都會沮喪消沉,但實際上他并沒有。某個大學生認為,如果他被分到一個自己不喜歡的宿舍,就會感覺很痛苦,實際上也沒有。
塞利格曼發現,像“從不”“總是”這樣的詞代表了持久性。就像把“抱歉”踢出我的詞匯表一樣,我也試圖不再使用“總是”“從不”,而是用“有時”“近來”來取代。我開始明白,無論我感到多么悲傷,下一個痛苦減輕的時刻總會來臨。這樣做也幫助我重新獲得了控制感。
我認識的一位精神科醫生解釋說,人類在進化中就具有聯結和悲傷的能力,人類有天然的工具可以從失去和創傷中復原。這一席話令我堅信自己扛得過去——既然人類進化出了應對痛苦的能力,那么悲傷就殺不死我。
每個人都會面臨失去:失去事業、愛情或生命。
問題不在于悲劇及挫敗何時發生,它們總會發生,我們也必須直面應對。
復原力源于每個人的內在,也源于他們獲得的外部支持;復原力源于因生命中的美好而引發的感恩,也源于在挫敗中學到的經驗;它既來自對于悲傷的解析,也來自對悲傷的接納。
有時,你的復原力比你想象的弱一些;有時,又會強一些。
我想讓你明白,當生活給你當頭一棒,讓你墜入悲傷之海時,你能做的就是奮力游向水面,重新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