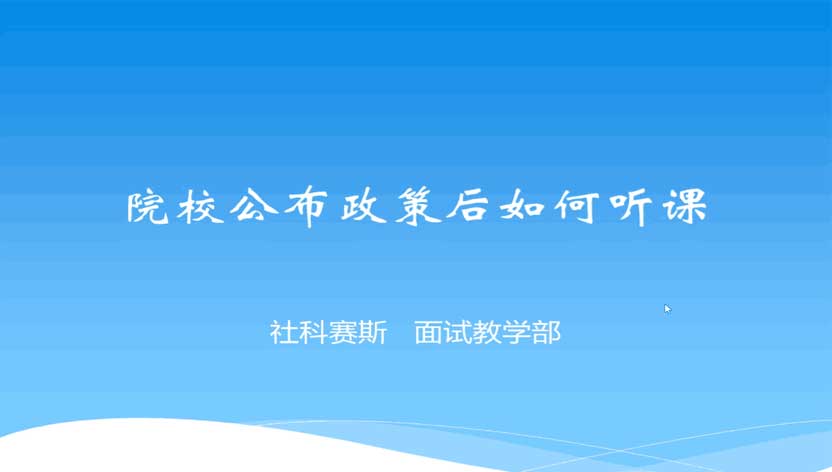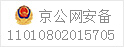2025MBA報考測評申請中......
說明:您只需填寫姓名和電話即可免費預約!也可以通過撥打熱線免費預約
我們的工作人員會在最短時間內給予您活動安排回復。
導讀:青年不僅是“會使用”互聯網的主力,而且還是“每天”都使用互聯網的主力。所以,中國的網絡社會,主要是以青年為特征的網絡社會。我們進行的網絡治理,就應該是精準瞄準于為青年服務的、以虛擬社會為特征而發出的網絡治理。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統計,截止到2016年12月,中國網民數量已達到7.3億,相當于整個歐洲的人口總量(預計今年年底會突破7.7億)。這就預示:在世界上,中國不僅是第一人口大國,而且還是第一網民大國。因此,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就既體現為對現實社會治理的現代化,也體現為對虛擬社會治理的現代化。為形成“網上與網下兩個同心圓”,響應習近平總書記4.19講話精神,我們有必要對中國網民的人口特征、上網行為、線上與線下組織狀況等進行系統梳理,以促進網絡治理的有效性。
網民參與和網絡社會
根據我們的調查(在全國隨機抽取了11000個樣本),在18-65歲之間人口中,能夠熟練使用互聯網的人數占比超過了50%。其中,在18-34歲之間的青年中,會使用互聯網人數占比為86.01%;在35-44歲的成年人中,會使用互聯網的人數占比為53.08%;在45-59歲的成年人中,會使用互聯網的人數占比為22.65%;在60-69歲的老年人中,會使用互聯網的人數占比為8.16%。與此同時,調查還發現:在經常使用互聯網的網民中,幾乎每天使用互聯網的人數百分比分布趨勢是:在18-34歲青年人為64.94%;35-44歲之間的成年人為49.66%;45-59歲之間的成年人為37.66%;60-69歲之間的老年人為26.15%——年齡越輕,每天上網的比率就越高。
因此,青年不僅是“會使用”互聯網的主力,而且還是“每天”都使用互聯網的主力。所以,中國的網絡社會,主要是以青年為特征的網絡社會。我們進行的網絡治理,就應該是精準瞄準于為青年服務的、以虛擬社會為特征而發出的網絡治理。中國經濟在進入新常態階段之后,中國社會也進入了以網絡社會為表征的新常態。只有認識這個以青年為核心的網絡社會的新常態,才能在適應的基礎上引領新常態。
通常,人們在現實社會的身份是明確的,能夠為管理部門所識別。但人們在虛擬社會或網絡社會的身份則是模糊的、是符號化的、而且還可能是易變的和多元的,即網民有將現實社會身份“如實”注冊為網絡社會身份的一面,也有隱蔽了現實社會身份而以虛擬化身份進入網絡社會的一面。在現實社會,一個人往往在同一時間只能出現在同一社會空間;但在網絡社會,人們則同時可以多元化地出入于不同的網絡空間,并根據自己的需要而角色化地活動于不同的網絡社區或網民人群。在現實社會,文化、宗教、習俗、制度規約、組織章程與法律等,往往會通過社會化作用將人們約束為“自我”以表現其社會特征;但在網絡社會,人們可能有時以“自我”的角色活動,但在大多數場合則是以“本我”的角色活動。網絡社會的無限性和多元時空性,使網民易于找到某種特征的“本我”群,或某種程度地模糊了“自我”與“本我”的虛擬群。
以青年為主要參與群體的網絡社會,還會將人們從現實社會的交往中析出而持續或間歇性地參與到超越時空的網絡社會之中,這也會使現實社會與網絡社會重疊為共時性,從而將現實社會與虛擬社會勾連在一起。網民不僅通過網絡完成消費與閑暇享樂,而且也通過網絡完成工作和信息交流——基于此結構化的日常生活,基于物質生產與物質生活建構起自己的“網絡意識”,并逐步形成網民的“網絡意識形態”。其中最具影響而又易于快速傳播的內容,便是以文本或聲像表達的、以評論方式跟帖的、通過信息加工與再造而衍生的“意見集合”。在現實社會,除媒體與特殊行業人員外,人們之間基本通過人際互動傳播信息并形成時代感的話語體系。但在網絡社會,人們的信息既會以人際單元傳播,但更多的卻表現為多元群體傳播——如果有必要,每個網民都可以將自己轉變為大眾傳媒以偏好性地形成網絡話語權或網絡話語體系。
網絡社會基礎與網絡意識形態的形成
人的社會性決定了網民的社會性。網絡參與和網絡活動的結果,必然形成聯系相對緊密的網絡群體,搭建起網絡社區的框架。所以,不管網民使用哪種類型的交往平臺,“交友活動”必然會構成網絡生活的基本內容。調查發現,在網民中,“幾乎每天都會”“交友聊天”的人群分布趨勢為:18-34歲的網民為67.13%,35-44歲的網民為47.54%,45-59歲的網民為33.02%,60-69歲的網民為18.91%。由此可以看出:年齡越輕,每天使用網絡交友聊天的概率就越大;反之,年齡越大,每天使用網絡交友聊天的概率就越小。網民通過交友聊天的方式組織起了網絡社會的基礎結構,由此向外擴展,將單個網民延伸為多個網民的社會集合,并在網絡社會中構筑自己的位置。
毋庸置疑,“交友聊天”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情感的寄托與分享,另外一方面還在于話語體系的建構與型塑。如果我們將活動于微信群或網絡社區的網民視為“熟人社會”的網民的話,那么,在對新聞閱讀后或在公共聊天室的直接跟帖評論,則是網民在“半熟人社會”或“陌生人社會”的言說。根據我們的調查,每天都會在不同網站發表評論(包括書寫文本與聲像言說)的網民年齡分布狀況為:18-34歲的網民占18.58%,35-44歲的網民占8.67%,45-59歲的網民占5.82%,60-69歲的網民占5.00%。從這里也可以看出,青年網民發表網絡評論的比率最高。在青年中,能夠邏輯表達自己思想的那些網民,主要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那些人。比如說,在34歲以下每天都會發表評論的青年網民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比為11.99%,“高中與中專”文化程度占比17.24%,“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為24.94%——這應該是非常高的比率。
因此,在現實社會有話語能力的人,在虛擬化的網絡社會同樣具有話語能力。要讓文化程度較低的人在網絡上短時間內清晰地以文字表達出自己的見解是比較難的。但在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網民中,每天都發表評論或在新聞事件的報道后積極跟帖,或進行比較激烈的文本爭論,則相對比較容易。以陌生人面孔進行的網絡評論之所以會形成相對較為集中的討論熱點,除現實社會的影響外,那些持續性寫作博客文章的、已經建立了話語權并影響了一定粉絲思維的意見領袖起著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
正因為如此,網民的世界并不像有些研究所說的那樣是完全平等的。在網民中,意見領袖與粉絲之間、話語強勢群體與無話語能力群體之間、信息依賴群體與信息發布群體之間會形成非常明顯的分層效應。在網絡社會中居于上層的階層,同樣希望將自己的意識形態擴展為整個網絡的意識形態。面對同一個社會熱點問題,為什么會表現出多元的論爭?就是因為各個不同的網民群體在爭奪話語權。一旦形成為網絡話語霸權,就會從信源和解釋力上占據意識形態的壟斷地位。因為網絡社會與現實社會既存在同構性,也存在區隔性,所以,網絡社會的意識形態與現實社會的意識形態并不必然劃一,有時甚而表現出非常激烈的、具有沖突意義的張力。在這種情況下,要使網絡更好造福于大眾,就必須研究其中的依賴關系,研究青年網民的語言習慣與信息生產與傳播過程,研究意見領袖的影響機制、研究網絡社會與現實社會的互動規律。
網民線上行為與線下行為的轉化
人們基于網絡社會而發生的網絡行為,會生成為現實社會的社會行為,從而將線上活動轉變為線下活動。對于某些固定的群體而言,其在網上活動的目的就直接服務于線下活動的組織。
調查發現,當問及“線上組織線下活動”時,“每周至少組織一次”的發生概率是:18-34歲之間網民為11.99%,35-45歲之間網民為5.49%,45-59歲之間網民為3.56%,60-69歲之間網民為2.25%。可見青年更易于通過線上組織線下活動。但線上網民群體的線下活動,終須群體成員的認同才得以發生,其中的關鍵因素,是群體核心成員的動員與組織,以及網民群體自身的經濟活動能力。“有錢”與“有閑”是線下活動得以開展的兩個主要客觀變量,而“愿意參與”則是線下活動得以持續的主觀變量。顯然,那些具有一定經濟能力、有時間支配彈性、有話語影響力的網民,才易于將線上活動轉變為線下活動。
調查數據也支持了這一點:在將18-34歲青年網民依照其受教育程度進行分類分析時發現,“每周都組織線下活動”的分布態勢是:“初中及以下”網民為6.88%,“高中與中專”網民為10.96%,“大專及以上”網民為16.92%。由此可見,文化程度越高,組織下線活動的概率也就越大。
因此,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青年,才既是網絡意識形態的生產者,又是網絡行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網絡社會的主導力量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青年,將網絡活動轉變為現實社會活動的主導力量,也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青年。這是中國網絡社會的基本國情,只有認識到這個基本國情,才能較好地認識網絡社會、把握網絡社會、引領網絡社會。
應該說,網民組織的絕大多數線下活動,是日常的生活化活動。但現實社會與網絡社會的互動特征,也會將現實社會的民生問題,通過網絡輿情的發酵轉化為網絡意識形態的部分內容,并藉此形成網絡動員,先形成“網絡圍觀”和“網絡評論”,激化為“網絡群體性事件”,然后將其轉化為現實社會的街頭政治。社會越是復雜,卷入的人群越是多元,現實社會與網絡社會對社會熱點問題的“求真”心理就越強,網絡信息的需求就越迫切,似是而非的信息的供給就越多。在這種情況下,經過加工的謠言與努力刻畫真相的故事都會競相爭奪話語權。于是,在較短的時間與空間中,事物變化的真相雖然重要,但網民偏好性的信息選擇、以及網民對信息的認同心理,才即時影響網絡意識形態的走向與網絡群體性事件向現實社會街頭政治轉化的可能。一句話,不是事物的本相決定網民的行動,而是網民相信事物具有何種本相才決定其發出何種行動。
正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那樣,隨互聯網特別是移動互聯網發展,社會治理模式正在從單向管理轉向雙向互動,從線下轉向線上線下融合,從單純的政府監管向更加注重社會協同治理轉變。需要知道,中國社會已進入網絡社會。網絡的發展以及“互聯網+”的拓展,會使現實社會與網絡社會更為顯著地形成“互嵌”結構。這就需要我們強化對網民特征、網絡社會基本結構、網絡意識形態、網絡社會與現實社會互動規律的認識。當前的最大問題,是克服那種只將網絡僅僅視為“新媒體”的狹隘觀點。只有將網絡社會看做是與現實社會同樣重要的一種新社會結構,我們才能順應時變、因勢利導、在了解青年的網絡參與、在把握青年網絡活動規律的基礎上,將現實社會與網絡社會的社會治理結合起來,系統解決好各種問題,維護好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促進網絡社會與現實社會的融合協調發展,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營造好“網上和網下兩個同心圓”。